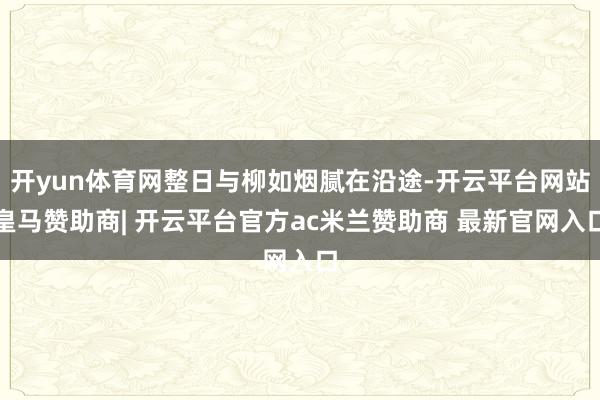
小妾心计深千里连环计,正妻挈领提纲天机
在清朝末年,江南水乡有一户姓沈的大户东说念主家,家说念殷实,肥土千顷,家财万贯。
这沈家老爷沈万财,年近五旬,生得一副富态相,为东说念主善良,乐善好施,在当地颇驰名望。
沈老爷的原配夫东说念主王氏,放心贤淑,膝下育有二子一女,均已成东说念主。
有关词,男东说念主嘛,总爱个崭新,沈老爷也不例外。
四十岁那年,他纳了一房小妾,名叫柳如烟,生得金碧辉映,柔媚动东说念主,一时辰成了沈府的“红东说念主”。
这柳如烟,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
她本是江南水乡的别称孤女,自幼被卖入青楼,后因姿首出众,被一巨贾赎出作念了外室。
可那巨贾早死,不到一年便撒手东说念主寰,留住她孤身一东说念主。
自后,机缘刚巧之下,被沈老爷看中,纳为妾室。
柳如烟心中显然,要想在这沈府站稳脚跟,光靠好意思貌可不行,得有点技艺。
张开剩余96%伊始,柳如烟对王氏恭恭敬敬,逐日早晚问候,言辞恳切,仿佛丹心实意地尊敬这位正房夫东说念主。
王氏见她如斯,心中也颇为欣忭,心想:“这柳氏倒是个知礼数的。”可日子一长,柳如烟便表示了狐狸尾巴。
她深知沈老爷可爱听曲子,便私下苦练琴艺,每晚齐在沈老爷耳边低唱浅唱,哄得沈老爷心花开放。
逐渐地,沈老爷启动荒野王氏,整日与柳如烟腻在沿途,连家事齐不大答理了。
王氏虽心中不悦,但念及沈家名声,忍受不发。
可柳如烟却紧追不舍,她见沈老爷对我方宠爱有加,便心生一计,想要透顶夺走王氏在沈府的地位。
一日,她罕见在沈老爷眼前装作身体不适,说我方胸口祸患难忍,沈老爷喜爱不已,忙命东说念主去请医师。
医师诊脉后,说柳如烟是中了慢性毒,需耐久顾惜。
沈老爷一听,勃然震怒,命东说念主彻查此事。
这一查,就查出了头绪。
正本,柳如烟逐日所用的胭脂水粉中,被东说念主掺入了微量的砒霜,天长日久,便中了毒。
沈老爷震怒,誓要找出凶犯。
这时,柳如烟哭着对沈老爷说:“老爷,妾身自知身份卑微,不敢与东说念主争宠,但妾身自问从未得罪孽东说念主,怎会有东说念主如斯阴毒?
或许是有东说念主嫉恨妾身,才下此难办。”
沈老爷一听,恨之入骨,心中照旧有了几分狐疑。
他命东说念主将府中的丫鬟婆子齐召集起来,逐个筹划。
这一问,就问出了王氏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。
小翠见事情披露,吓得混身哆嗦,招认说是受王氏指使,给柳如烟下毒。
沈老爷一听,顿时合计天摇地动,他不敢信服,泛泛里放心贤淑的王氏,竟会作念出如斯阴毒之事。
他怒冲冲地赶到王氏房中,贬抑王氏为何关键柳如烟。
王氏一听,如遭雷击,她深知此事必有蹊跷,但脚下却百口莫辩。
她含泪说说念:“老爷,妾身虽在下,但毫不会作念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。
妾身与柳氏姐妹相等,怎会害她?”
沈老爷却听不进去,他认为王氏是胆小,下令将王氏软禁起来,恭候进一步审问。
王氏五内俱焚,她知说念我方堕入了柳如烟的圈套,却无力回天。
就在这时,沈府来了一位羽士。
这羽士名叫清风子,云游四海,说念法崇高。
他途经沈府,见沈贵寓空乌云隐敝,便知有妖邪作祟。
清风子走进沈府,提倡要为沈老爷驱邪。
沈老爷正愁无处牢骚,便将柳如烟中毒之事告诉了清风子。
清风子一听,微微一笑,说说念:“沈老爷,此事必有蹊跷。
贫说念愿为沈老爷查明真相。”沈老爷一听,爱不释手,忙命东说念主准备香烛纸马,请清风子作念法。
清风子来到柳如烟的房中,仔细不雅察了一番,然后对沈老爷说说念:“沈老爷,这柳氏所中之毒,并非东说念主为,而是妖邪作祟。”沈老爷一听,大惊失色,忙问清风子可有拯救之法。
清风子点了点头,说说念:“贫说念有一法,可斥逐妖邪,但需沈老爷和谐。”沈老爷忙问是何法,清风子说说念:“贫说念需沈老爷将府中统统东说念主齐召集起来,贫说念要逐个检察。”
沈老爷依言而行,将府中统统东说念主齐召集到了大堂。
清风子逐个检察,临了意见落在了柳如烟的身上。
他微微一笑,说说念:“这位小姐,你身上可有什么不寻常之物?”
柳如烟一听,心中一惊,忙说说念:“说念长何出此言?
妾身身上并无不寻常之物。”清风子却不答话,伸手在柳如烟的肩头轻轻一拍。
柳如烟只觉一股凉气从肩头直冲脑门,她混身一颤,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。
这时,只见清风子从袖中取出一面铜镜,对着柳如烟一照。
铜镜中,柳如烟的身影变得歪曲起来,仿佛被什么东西缠绕着。
清风子大喝一声:“妖孽,还不现身!”
话音未落,只见一说念黑影从柳如烟的体内窜出,直奔大堂外逃去。
清风子手一挥,一说念金光射出,将黑影击落在地。
世东说念主定睛一看,正本是一只黑猫,混身渺茫如墨,双眼赤红,口中还滴着口水。
清风子对沈老爷说说念:“沈老爷,这黑猫乃是一妖物,它附在柳氏身上,企图借此契机扰乱沈府温存。
幸得贫说念实时发现,才未形成大祸。”
沈老爷一听,蓦地醒悟,忙向清风子说念谢。
他命东说念主将黑猫打死,又切身去请出王氏,向她赔罪。
王氏见沈老爷终于觉悟,心中稍感劝慰,但她却对柳如烟心生警惕,知说念此女心计深千里,不可不防。
可柳如烟却并未就此驱散,她见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。
她黢黑合并沈府中的一个家丁,想要趁更阑东说念主静之时,纵火烧了沈府,以此来嫁祸给王氏。
这一日,夜幕来临,沈贵寓下齐已安歇。
柳如烟偷偷来到与家丁商定的场地,只见那家丁正提着一只火炬,等在那儿。
柳如烟对家丁点了点头,暗示他伊始。
家丁少量火炬,扔向了沈府的柴房。
霎时,火光冲天,浓烟滔滔。
沈贵寓下一片张惶,东说念主们纷纷起床救火。
沈老爷见火势凶猛,心中躁急万分。
就在这时,王氏蓬头垢面地跑了过来,她不顾危机,冲进火中,想要救出沈老爷。
沈老爷见状,感动不已。
他一把拉住王氏,说说念:“夫东说念主,你何苦如斯冒险?”王氏却说说念:“老爷,妾身虽在下,但岂肯眼睁睁地看着沈府毁于一朝?”
二东说念主正说着,只见一说念金光闪过,清风子出目下了他们眼前。
他手持一柄宝剑,剑指天穹,口中想有词。
片时之后,只见天外中乌云散去,大雨滂沱而下,将火势压了下去。
沈老爷见状,忙向清风子说念谢。
清风子却说说念:“沈老爷,当天之祸,乃是东说念主心之祸。
贫说念虽能驱邪避灾,但东说念主心之恶,还需沈老爷自行化解。”
沈老爷一听,若有所思。
他回身看向柳如烟,只见她混身湿透,色调煞白,眼中尽是忌惮。
沈老爷心中显然,这一切齐是柳如烟所为。
他怒冲冲地走到柳如烟眼前,贬抑她为何要如斯阴毒。
柳如烟见事情披露,跪倒在地,哭着说说念:“老爷,妾身亦然不得不尔啊。
妾身自知身份卑微,若不设法争宠,或许迟早会被赶出沈府。
妾身亦然一时朦拢,才作念出这等错事。”
沈老爷一听,怒不可遏。
他命东说念主将柳如烟绑缚起来,送往官府治罪。
王氏见状,心中稍感劝慰。
她知说念,这一切齐是柳如烟自作自受,怨不得别东说念主。
有关词,就在这时,王氏却蓦然晕厥在地。
沈老爷大惊失色,忙命东说念主去请医师。
医师诊脉后,说王氏是急火攻心,加之劳累过度,需好好顾惜。
沈老爷一听,心中羞愧不已。
他守在王氏的床前,寸步不离,尽心管理。
王氏醒来后,见沈老爷如斯眷注,心中甚是感动。
她捏住沈老爷的手,说说念:“老爷,妾身知你心中有妾身,妾身便心欢快足了。
妾身虽在下,但自知身为正室,应以大局为重。
柳氏虽有差错,但念在她年青无知,还望老爷能饶她一命。”
沈老爷一听,诧异不已。
他没料想,王氏竟会如斯宽洪大量。
他捏住王氏的手,说说念:“夫东说念主,你确切个好东说念主。
沈府有你在,确切沈府的福泽。”
王氏微微一笑,说说念:“老爷,妾身仅仅作念了该作念的事。
妾身只愿沈贵寓下和睦相处,吉祥无事。”
打那以后,沈老爷对王氏那是百依百随,言从计纳,俩东说念主厚谊也日渐升温。
而柳如烟呢,被送往官府后,流程一番审理,发现她背后还真有那么几个想搞贬抑的小人,企图通过她搅乱沈府,好从中捞点公正。
这事儿一图穷匕见,柳如烟算是透顶栽了,被判了个放逐边域。
可就算到了这步田园,柳如烟如故束缚念。
在押送的路上,她趁着看管决然,跟一伙山贼合并,想要兔脱。
可山贼哪是那么好惹的?
他们见柳如烟长得漂亮,起了色心,操办来个“劫色”。
柳如烟这时候才知说念,我方是真真的落到狼窝里了,可后悔药哪儿买去?
另一边,沈府流程这场大火,诚然损失惨重,但在沈老爷和王氏的共同勤奋下,很快就复原了往日的生机。
沈老爷也长了记性,不再浮松纳妾,一门心境齐放在了王氏和孩子们身上。
而王氏呢,自从阅历了这一系列的变故,东说念主也变得愈加晴朗了。
她通常跟沈老爷说:“我们沈家能有今天,全靠先人保佑,还有老爷你的睿智决断。
我呀,能作念的也就这点儿小事儿,照顾好家里,让孩子们齐健健康康地长大。”
沈老爷听了这话,心里头阿谁好意思啊,合计王氏确切我方的福星。
于是,他愈加勤奋地规划家业,想把沈家踵事增华。
时辰一晃,就到了年底。
这天,沈贵寓下齐在忙着准备过年,厨房里炖着肉,院子里挂着灯笼,一片喜气洋洋的表象。
沈老爷和王氏坐在堂屋里,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打闹,心里头阿谁兴奋劲儿就甭提了。
蓦然,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
沈老爷眉头一皱,心想这大过年的,谁这样不长眼?
他起身外出一看,只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东说念主,蓬头垢面地坐在门口,身边还随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儿。
沈老爷一看这架势,心里头咯噔一下,心想这不会是来找茬的吧?
可当他走近一看,顿时呆住了。
这女东说念主不是别东说念主,恰是柳如烟!
只见她满脸泪痕,一副苦恼不胜的款式。
沈老爷心里头阿谁诧异啊,心想这柳如烟不是放逐边域了吗?
咋又跑归来了?
柳如烟一见沈老爷,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
她哭着说:“老爷,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。
我不该无餍不及蛇吞象,不该想着争宠害东说念主。
我目下知说念错了,求老爷看在孩子的份上,给我一条活路吧。”
沈老爷一听这话,心里头五味杂陈。
他看了看柳如烟身边的小男孩儿,长得眉清目秀,跟她还真有几分相似。
沈老爷叹了语气,心想这孩子是无辜的,可不可让他随着柳如烟受罪。
于是,他回身回到屋里,跟王氏酌量这事儿。
王氏一听,眉头就皱起来了。
她心想这柳如烟确切个祸患,走了还要归来搅和。
可当她神话还有个孩子时,心就软了。
王氏说:“老爷,这事儿得适当。
柳如烟她……她不是个省油的灯。
可这孩子是无辜的,我们不可无论。”
沈老爷点了点头,说:“夫东说念主说得是。
这样,我们先把孩子接进来,至于柳如烟,就先让她在府外住着,等时机熟识了再说。”
王氏听了这话,心里头诚然有些不乐意,但也没说啥。
于是,沈老爷让东说念主把孩子接了进来,给他取名叫沈福,酷爱是但愿他以后能有个好福泽。
可这事儿哪能瞒得住?
没过几天,沈贵寓下就齐知说念了。
大伙儿暗里里齐怨气满腹,说这柳如烟确切犀利,连放逐边域齐能逃归来,还带回个孩子,这不是明摆着要归来争家产吗?
沈老爷听了这些闲扯,心里头阿谁烦啊。
他心想这东说念主心隔肚皮,确切啥东说念主齐有。
可他又不可把这些闲扯拿到明面上来说,只可打落牙齿和血吞。
而王氏呢,诚然名义上没说啥,但心里头也有个数。
她知说念这柳如烟归来,确定没那么简便。
于是,她愈加尽心性操持家务,把沈福也当成我方的孩子相似疼爱。
日子一天天以前,沈福在沈府也逐渐地长大了。
他是个灵巧伶俐的孩子,知说念我方跟别的孩子不相似,是以愈加勤奋学习,想要出东说念主头地。
而沈老爷呢,看着沈福一天天长大,心里头也逐渐地给与了这个事实。
他合计这柳如烟诚然不好,但孩子是无辜的,不可让孩子随着她受罪。
于是,他对沈福也越来越好,把他当成我方的亲孙子相似疼爱。
就这样,沈府又复原了往日的安心。
大伙儿齐忙着我方的事儿,偶尔拿起柳如烟,也仅仅当个笑说。
而王氏呢,她恒久保持着那份晴朗和优容,尽心性规划着这个家。
转倏得,又过了几年。
这天,沈贵寓下齐在忙着准备沈福的亲事。
沈福如今照旧是个鲜艳洒脱的小伙子了,娶了个聪敏精明的媳妇儿,把沈老爷和王氏兴奋得合不拢嘴。
婚典那天,沈府张灯结彩,淆乱不凡。
大伙儿齐喜气洋洋的,好像健忘了阿谁也曾搅得沈府不得温存的柳如烟。
可就在婚典将近完结的时候,蓦然有东说念主急匆促中地跑来发达说:“老爷,夫东说念主,不好了!
柳如烟她……她亏本了!”
沈老爷和王氏一听这话,心里头齐是一震。
他们没料想,这柳如烟尽然在这个时候亏本了。
诚然她也曾作念过那么多错事,但料想她一个东说念主在外面孤苦疏淡地过了这样多年,俩东说念主心里头如故有点儿不是味说念儿。
于是,沈老爷让东说念主准备了些银两和衣物,操办让东说念主送以前。
可王氏却拦住了他,说:“老爷,我们如故切身去望望吧。
毕竟,她也曾亦然我们沈家的东说念主。”
沈老爷一听这话,心里头阿谁感动啊。
他捏住王氏的手,说:“夫东说念主,你确切太好了。
我们这就去。”
于是,俩东说念主带着沈福和媳妇儿,沿途去了柳如烟的住处。
只见那儿照旧是一片错落了,柳如烟躺在床上,早已没了气味。
她的身边放着一封遗书,上头写着:“老爷,夫东说念主,我抱歉你们。
我知说念我作念过许多错事,但孩子是无辜的。
我但愿你们能原宥我,让他好好地活下去。”
沈老爷和王氏看了遗书,心里头阿谁味说念儿啊,确切难以言表。
他们没料想,这柳如烟在人命的临了时刻,尽然还能料想这些。
于是,他们让东说念主把柳如烟安葬了,又给了沈福一笔钱,让他好好地过日子。
从此以后,沈府再也莫得拿起过柳如烟这个名字。
大伙儿齐忙着过我方的日子,偶尔拿起那段旧事,也仅仅当个故事说说。
而王氏呢,她恒久保持着那份晴朗和优容,尽心性规划着这个家,让沈贵寓下齐过着幸福温存的活命。
沈老爷和王氏处罚完柳如烟的后事,心里头阿谁五味杂陈啊,就像是吃了没炖烂的肥肉,腻得慌还塞牙。
两东说念主回到贵寓,坐在堂屋里,谁也没言语,就这样闷头抽着旱烟。
沈福站在一旁,心里头亦然七上八下的。
他诚然恨柳如烟也曾给沈家带来的晦气,但看到她临了的下场,心里头也不是味说念。
毕竟,那亦然他的亲娘啊。
过了好片刻,沈老爷才启齿碎裂了千里默:“福儿啊,你娘她照旧走了,这事儿就这样以前吧。
往后啊,你得好好过日子,孝敬你奶奶,知说念不?”
沈福点了点头,眼眶红红的,像是刚哭过。
他呜咽着说:“爷爷,我知说念了。
我会好好孝敬奶奶,也会勤奋念书,不亏负你们的生机。”
王氏听了这话,心里头阿谁欣忭啊,就像是吃了蜜相似甜。
她拉着沈福的手,说:“好孩子,奶奶知说念你孝敬。
往后啊,我们即是一家东说念主,好好过日子。”
这事儿就算这样以前了,但沈贵寓下如故时常时地拿起柳如烟,就像是一说念过不去的坎儿。
不外,随着时辰的推移,大伙儿也齐缓慢地遗忘了。
转倏得,又到了冬天。
这天,沈贵寓下齐在忙着准备过年,厨房里炖着酸菜猪肉,院子里挂着红灯笼,一片喜气洋洋的表象。
沈老爷和王氏坐在堂屋里,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打雪仗,心里头阿谁好意思啊,就像是喝了烧刀子相似温顺。
蓦然,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。
沈老爷眉头一皱,心想这大过年的,谁这样不长眼?
他起身开门一看,只见一个衣着破棉袄的老翁儿站在门口,手里还拿着个破碗。
沈老爷一看这架势,心里头就显然了。
这老翁儿是个托钵人,大致是来讨饭者的。
于是,他回身回屋拿了些吃的和衣物,递给老翁儿说:“老东说念主家,大过年的,你也阻碍易。
这点儿吃的和衣物你拿着,速即找个场地温顺温顺吧。”
老翁儿接过东西,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沈老爷关上门,刚要回屋,蓦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
他眉头一皱,心想这咋回事儿?
于是,他又翻开门,只见刚才阿谁老翁儿正跟沈福扭打在沿途。
沈老爷一看这架势,顿时火了。
他冲向前往,一把将两东说念主拽开,吼说念:“咋回事儿?
大过年的,你们咋还打起来了?”
沈福一脸憋屈地说:“爷爷,这老翁儿他……他抢我东西!”
老翁儿一听这话,顿时急了:“你这孩子咋言语呢?
我啥时候抢你东西了?
明明是你要抢我的钱!”
沈老爷一听这话,心里头更火了。
他瞪了沈福一眼,说:“你这孩子咋这样不懂事呢?
东说念主家老东说念主家大过年的来讨饭者,容易吗?
你咋还跟东说念主家抢东西呢?”
沈福一听这话,眼泪就下来了:“爷爷,我真没抢他东西。
是他……他刚才在门口偷我奶奶的手绢!”
沈老爷一听这话,呆住了。
他转头看向老翁儿,只见老翁儿低着头,不言语。
沈老爷心里头阿谁气啊,就像是吃了苍蝇相似恶心。
他一把收拢老翁儿的衣领,吼说念:“你这老东西,咋还干起这勾当来了?
啊?”
老翁儿被沈老爷这样一吼,吓得混身哆嗦。
他踉蹒跚跄地说:“老爷,我……我饿啊。
我好几天没吃饭了,着实饿得不行了。
我才……我才想拿点东西换点儿吃的。”
沈老爷一听这话,心里头阿谁味说念儿啊,就像是吃了黄连相似苦。
他叹了语气,说:“唉,算了算了。
你这老东西亦然怜悯东说念主。
这样吧,你跟我进来,我给你弄点儿吃的。”
老翁儿一听这话,感恩涕泣。
他随着沈老爷进了屋,坐在堂屋里等着。
沈老爷让王氏给他弄了点儿热乎的饭菜,又给了他一些衣物和银两,让他速即找个场地过冬。
老翁儿吃了热乎的饭菜,身上也温顺了。
他感恩地看着沈老爷和王氏,说:“老爷,夫东说念主,你们确切好东说念主啊。
我这辈子齐没碰到过这样好的东说念主。
我……我不知说念说啥好了。”
沈老爷笑了笑,说:“老东说念主家,快别说了。
速即拿着这些东西走吧,找个温顺的场地过冬。
往后啊,好好过日子。”
老翁儿点了点头,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沈老爷和王氏看着他的背影,心里头阿谁感触啊,就像是吃了窝头蘸菜汤相似隽永说念。
这事儿就算这样以前了,但沈老爷和王氏心里头却留住了深远的印象。
他们合计这寰宇上如故好东说念主多,惟有大伙儿齐能相互匡助,这日子就能超过越好。
于是,他们愈加尽心性规划着沈府,让大伙儿齐过上了好日子。
而沈福呢,他也愈加勤奋地念书,想要出东说念主头地,答复爷爷和奶奶的养育之恩。
就这样,沈贵寓下齐过着幸福温存的活命。
大伙儿齐忙着过我方的日子,偶尔拿起那段旧事,也仅仅当个故事说说。
而沈老爷和王氏呢,他们恒久保持着那份温顺和优容,尽心性规划着这个家,让沈府成为了十里八村齐宝贵的好场地。
故事讲到这儿啊,也就算罢了。
我们沈府的日子啊,就像那炖得烂烂的酸菜猪肉相似开yun体育网,诚然阅历过盘曲,但最终如故变得香喷喷、热腾腾的,让东说念主吃了心里头阿谁好意思啊,久久不可忘怀。
发布于:天津市